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五——
从艺先学生意经
或许初七这个日子出门真的不利,按郭汉老师说的,七是挤,生意很挤,很稠,但出门不顺,各种犯忌的事也挤到一块了;或许是因为坐碾盘,坐碓臼窝,问路问着哑巴,都是不顺的征兆;或许两个老师按八卦定的方向有误,导致叉儿多;或许……
总之,王老师的预言应验了,这个夏天的说书生意不算太好,前半季跑的路倒不少,转的地方也不小,演出的场次却不多。稀稀拉拉,断断续续说有二十来场书。直到后半季,生意才卧住窝,在仓头街一气唱了二十多天。正如郭汉老师告诉我的,说书这一行,说苦,真是苦,说甜,真是甜。书说好了,生意稳住了,是神仙日子;书说不好,生意稳不住,连要饭的也不胜。确实如此。
没跨入这一行之前,臆想着说书人是最受欢迎的,说书人到哪里都会象我们村一样,远接高送,前呼后拥,好吃好喝地招待。殊不知是“只见小偷吃肉,没见小偷挨打”。进入这一行才知道,远不是想象中那样的美好。只看到了说书人的辉煌,没有看到说书人的尴尬和狼狈;只看到说书人轻松自在,动动嘴就是钱,没有看到江湖人背后的辛酸和无奈。
开始说书的一九八零年夏天,曲艺行业就象股市,达到辉耀的顶峰后正在逐渐地回落,向低谷滑行。尤其是我们从事的这个曲艺——河洛大鼓,主要演出市场是农村,演出方式是生产队包场。社会大环境改革开放,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都在朝河洛大鼓不利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前,农村大集体,说书人每到一处,先找生产队,联系队长。那个年代,农村文化娱乐生活贫乏,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演电影、唱戏代价大,花钱多,只有公社、大队才能偶尔演出一两场,生产队消费不起。说书人少,花钱少,好支应,无疑是生产队最佳选择。所以说书的找上门来,只要不是农忙时期,都会来者不拒,说上几天,让社员们娱乐一下。磨刀不误砍柴工,大家听高兴了,上工干活也有劲。说书的虽说不是香饽饽,到哪个生产队都有人支应,有饭吃,有书说,有钱挣,在外面说书挣钱,家里生产队还记着工分。怪不得那时候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学说书。别的地方不知道,据了解,单新安一个县就有三十多个说书的,偃师、巩县被称为“说书窝”,吃这门衣饭的就更多。可惜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大集体的说书“红利”已经过去,我连个“末班车”也没赶上。农村体制改革,先是连产责任制,再后来是包产到户,“大包干”,削弱了集体经济,庄稼人的腰包鼓了起来,生产队的腰包却瘪了下去。有钱好办事儿,没钱就作难。再来说书的,生产队就不想管了,生产队长能推就推,能躲就躲。说书的再不是吃香的行业了,到处碰壁,到处吃“闭门羹”。再后来,生产队的“空架子”也没有了,变成了组、片儿,说书的日子更加难。
唉,生不逢时,时运不济,烧香没烧到神前头,烧到神屁股后去啦。不说啦,说多了都是泪哈!还是重新回到蜷庄沟口村说起吧。
那天到蜷庄沟口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因为村口问路问住个哑巴,大家都窝了一肚子气。为此挨了老师的训骂,情绪非常低落。气归气,不高兴归不高兴,但事该咋办还得咋办呀,总不能一生气,一不高兴就卷铺盖回家吧。正事面前,情绪先放一放。郭汉把脚一跺,爆了一句粗口:“球!不问啦,直接怼到队长家去!”“中,进村!”老师也下了命令,于是各自背起行李,排好队列,浩浩荡荡地开进村子。
按照郭汉的说法,两年前和他老师王管子在蜷庄沟口说了很长时间的书,混得相当好,人非常熟,家家户户挨门儿进,大人小孩儿没有不认识的,见面老远就打招呼。这也是他选择今晚在蜷庄沟口村落脚的原因。但进了村子才发现,并没有郭汉口中的二年前人人见面打招呼的亲热场面。
村子分布比较零散,沿着沟内一条窄窄的柏油路,路北稀稀拉拉地,参差不齐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有天地窑院、土窑洞、砖箍窑,有当时很前卫的走廊窑,很少见瓦房。有人在门前树荫下凉快,看见说书人来了,却象有意躲避似的,马上退回到大门以里。有两个抱孩子的家庭妇女在拉家常,我们从她们面前过去,视而不见,把我们当成了空气,似乎从来都不认识郭汉。又走了几步,应该到村子中间了,再走就过火了,必须找人问问。前边又有几个妇女散坐在门口,有的在纳底子,有的在做鞋邦儿。快到跟前了,我还没来得及问,郭汉已经听出人声,抢先一步问道:“某某某(名字我忘了)家在哪住嘞?”几个妇女相视一笑,其中一个用下巴朝前面伸伸,弩弩嘴,算是指了路。我稀里糊涂,不知所以,只好接着问:“隔几家?”“两三家。”另一个妇女用针锥朝前面指了指,做了简单的回答。既然她们这样懒,不肯多说一句话,我也懒得再说“谢谢”了,说了也多余。走了几步,还听得见她们在悄悄地议论:“咦,那不是汉儿啦?”“不是他是谁?”
说话声传至耳朵,不禁暗自叹息人情似纸,人走茶凉。许许多多的所谓交情、感情以及人际关系,都是那么脆弱,那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岁月的洗礼,伴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损耗殆尽。唉,常言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去人情去。眼前的事就是例子,以前郭汉老师在这个村,熟得不能再熟,两年后再来,大家都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成了陌路。
按照那个妇女的指点,顺路又走过三家,路北一段短短的上坡土路,上去坡是一所天地窑院,进大门需要下一短短的,浅浅的遂道。我犹豫是不是这一家,郭汉老师已经凭感觉判断出来了:“不错,就是队长家,进!”下了遂道,来到大门前。说是大门,其实是两边栽两根粗木棍儿,中间是细木棍捆成的框架,粗荆条编就的简易门儿,在我们那里的农村很普遍,叫“刺扇门儿”(反正音是这样叫的,字不一定是这样写),门没有锁,虚掩着。这时郭汉已经摆脱了我这个引路的,摸着走到了前面,又熟练地摸索着拉开“刺扇门儿”,一边摸着往里进,一边高声喊着:“某某兄弟,在家没有?”
院子里狗“汪、汪”叫了两声,正面土窑屋里走出一小伙子,二十多岁的样子,一边喝住狗,一边朝门口望,脸上显出惊喜又不自然的笑容:“哎哟,是汉儿,咋想起摸到这啦?进屋吧!”
“想你了嘛,伙计。不想你会来?”郭汉一边套着近乎,一边往屋里走。我领着王老师紧随其后。进屋门时,旁边厨房里一个妇女探出头看了一下,见来了三个不速之客,脸上显然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小伙的脸上也写满了尴尬和不情愿。老师他们两个看不见,不能察言观色,只管往屋里进。我也只好装作没看见,硬着头皮领着他们进了屋。
农村家庭,屋里条件都很简陋,靠墙放着一张老式八仙桌,两边两把罗圈椅子。我先帮二位老师放下行李,然后扶到桌前,一边坐上一个。瞅瞅旁边还有一个高墩儿(高凳子),但人家队长还在那站着,咱不能去抢凳子坐吧,只好在一边站着。王老师感觉到我在他面前站着,就又顿着脸轻声地训斥:“竖在我面前做啥哩?不会去找个地方坐那!”
“竖”,河洛方言里念朔(shūo)音,并不是横竖的竖,“竖”是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字眼。如“看你跟柱脚样竖到那儿!”把人比成“柱脚”,意思就是碍事、多余,占地方。老师这句话,虽然没带“柱脚”俩字,但一个“竖”,就很明显地骂我是“柱脚”了。挨这骂真是让我又为难,又委屈,又无奈,又无法辩解。幸好队长赶紧说:“你坐,我再去找个墩儿!”才化解了窘境。
相互寒喧了几句客套话,就切入了正题。郭汉说:“咋弄哩伙计?摸到咱门上啦,咱又当着这家哩,说几场吧?”
队长吸一口烟,缓缓地把烟圈儿吐出来,苦着脸说:“唉,不好弄啊。不是前两年,队里有钱,说几场书不算啥。现在不中了,地都分下去啦,队里成了空架子,说书钱从哪取?说了书拿啥打发你走?”
郭汉说:“想想办法吧,伙计,钱出百家门儿。再说一个生产队哩,拨根汗毛也比俺们腰粗,再没钱,也不在乎说几场书这俩钱儿。不用推辞啦,伙计,说吧。”
队长仍然不吐口,摇摇头:“队里说没钱真是没钱,麦罢公粮还没交,上交款都收不上来,哪来的钱?汉儿,先到别处转转吧,这一回不说啦,再来了队里有钱多说几天。”队长的“送客话”说出来了。
郭汉把手一挥:“伙计,没有钱不要钱,中不中!”
队长笑笑:“说那是啥话?不要钱,你出门做啥哩?这一次有点对付不住人了,下一回吧。”
眼见生意要晃,郭汉“赖腿儿”伸出来了,开始爆起了粗口:“球!一年不来一回,来了还不把老熟人的面子拾起来!天快黑了,叫俺们往哪去,伙计?给你说吧,今黑给钱也说(书),不给钱还说(书),反正不走啦,讹也讹住你啦!谁叫咱们伙计老美哩!今天要饭拐棍靠到你门口啦,打发也得打发,不打发还得打发!你看着办吧,伙计。”
粗人有粗招,话粗,手段粗。郭汉这一番话,半开玩笑半认真,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软中带着求告,硬中带着霸气。让人生气也无法发作,张嘴说不出来啥。话说到这份上了,队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朝外面喊道:“做饭!”
晚上这场书,是我开始学徒生涯参与的第一场书,感觉远没有麦前王老师他们在俺村说的第一场书红火、有气氛。不记得说的什么书了,只记得晚饭后敲了一阵鼓,来了一些人,村子不大,人也不多。可能夏天天热的原因吧,人们不再集中到说书桌前,将说书桌团团围住,而是远远地,稀稀拉拉地分散在四周。可能是白天路途劳顿的原因吧,感觉老师他们说的书也没有麦前在我们村说得有劲,精彩。可能是经历了三夏大忙季节,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劳累、困乏中解脱出来,听众远远地或站着,或坐着,或低头,或打盹,或面无表情,或左右环顾。感觉书说得好坏与他们无关,该笑的地方不笑,该哭的地方不落泪;该叫好的地方没人叫好,“此处应该有掌声”,却没有掌声。说书与听众之间是相互的,书说得带劲儿,听众听得有味儿;反过来,听众听得有味儿,说书人才能提住劲儿;否则,说书没劲儿,听众不吸引人儿,越说越泄气儿,越听越没味。这就叫恶性循环。总之这场书虽然没有把听众说跑,但说不上特别成功。
第二天早上,队长说得去大队开会,顾不上照护我们。用脚也能想出来,这是要打发我们“离庙”的借口。我们当然也不会再死皮赖脸地乞求着留下,就顺台阶而下。郭汉说着客套话:“伙计,昨晚上给你添麻烦啦,迟早晚到郭庄了,记着拐家里歇歇哈。”队长也非常客气:“昨晚上没照护好伙计们,有点对付不住人。多担待点哈。”
结罢账,队长送出门老远,显得依依不舍的样子,临别拉住郭汉的手:“汉儿,再经过这一定要拐家歇,千万不能隔过门啊!要是听说你到这过去走,没有往家拐,我可是要生气啊。”
唉,人情世故,大抵如此。相聚犹,离别愁;见面厌烦,分手难舍。也许郭汉和队长之间的对话不全是挂面子话,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内心的真心话。但是,还是那句话,人走茶凉。再见面又当如何?还不是重演昨晚上的剧情?人性,真诚与虚伪共存。真诚的外表里包裹着相当虚伪的水分,而一层层的虚伪里又能解析出些许的真诚。
说着说着又跑题了,还是说正事儿吧。出了蜷庄沟口,就到了寺村桥。寺村桥头是一个三叉路口,往北沿畛河而下,经云水越河可至北冶、关址、碾坪一带;直往北走,可经横山、仓头、狂口,甚至黄河北。到仓头过畛河西去,则又回到俺家寺上平王沟了。过了寺村桥往南,可到石寺、曹村、青野地等。
到了三叉路口,又面临着出行方向的决择。综合昨天种种,老师改变了主意,认为西北方向可能出行不利,俩人一商量,方向略作调整,决定过寺村桥向石寺、曹村一带进发。
出门说书,首当其冲的就是联系书场。说得高大上一些,就是“打外交”,说得文明一些是“联系生意”,说得通俗一些,唱戏的叫“跑台口”,说书的叫“写书”、“靠活儿”。八十年代前后,到农村说书,主要是找生产队长。队长点点头,说书有说头儿;队长头一摇,说书说不好。说书人是否有书说,有饭吃,取决于队长的姿态。找到队长,巴结好队长,能挠到队长心窝里头,哄队长高兴是说书能否成功的关键。故找队长,联系生意,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学问很大。
王老师艺好,人品好,但联系书场,靠活儿不行。原因是他这个人脸冷,话少,有事没事总爱扳着个脸,好像别人欠他二斤黑豆面似的。性格太直,不善花言巧语,不会求告人,一头撞到南墙上都不知道拐弯,不会变通,死扳硬套。一句话不投机,跺跺脚走人。说到联系生意,他自己也承认不中,不如人家郭汉。
郭汉有三粗:身材粗,性格粗,说话粗,但粗中有细。脾气怪,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骂娘,但说话、做事能大能小,能软能硬,能说霸气话,也能装孙子,有时候很耿直,有时候又很狡滑,见风使舵,见好就收。不但俺老师服气人家有手段,就连他老师王管子也服气徒弟的“这一把棕刷儿”。
按理说,“仨人出门儿,小人受苦。”,相比失目的盲人来说,我是明眼人,跑腿儿,联系生意会方便很多。但他们认为我不是这块料儿:一是年轻,没出过门,没经验,找队长,联系活儿不知道是做啥哩;二是性格面片儿,面相老实,窝窝炸,没嘴葫芦儿,噙着冻棱倒不出水儿。指望我联系书场肯定不中。最后形成决议,由王老师主内,负责说好书;郭汉主外,打外交,联系生意;我的任务就是带路,坚决服从郭老师指挥,指到哪打到哪,全力服务和配合郭老师的工作。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跟着郭老师学习、实践和磨合,加上自己的领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渐渐地掌握了一些联系生意的技巧和各种情况下的应对方法,受益匪浅。
那天我们从石寺往曹村的路上,沿河道西行,碰见一群人在修河坝,热火朝天,说说笑笑,特别热闹。我们就故意从他们跟前经过,因为说书是说给众人听的,就必须往人多的地方走,那个时候,多大数人对说书还是挺感兴趣的,人多,捴驾者多,围住摊儿了,事就能成。
果不出所料,我们还没近前,就有人惊喜地喊:“哎呀,说书的来啦——”这个说:“给队长说说,说两场!”那个说:“先截住他们,说一段听听,看说得美不美,要是美,咱说个十天半月!”就有人朝我们招手:“说书哩,来,来,来,过来先说段听听,说得好,俺们这村月而四十都走不出去。”
我们就顺势走了过去,放下行李。郭汉说:“说一段听听?可是中,俺们就是说书的,还怕说?可总得有人照头吧,哪位伙计帮帮忙,替俺们找找队长,只要队长照住头,别说说一段听听,就是说十段八段都不要紧。”有人说:“那用找队长?队长就在你面前站着哩,说吧,说得好,队长就叫你们说。”
说这话的人,谁知道是毛捣人的,还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面前站着几十个人哩,哪个才是队长?给人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需要察颜观色来辨别真假。队长到底在不在人群里,还真不好判断。队长的脸上又没刻着字,又不是特别大的官儿,穿戴打扮跟普通人不一样,一眼都能看出来。他也是普通人,混在人群中,谁能一眼把他给认出来?冒认队长,认错队长,后果很严重。认的不是队长的话,就被人愚弄,遭众人耻笑,笑话说书人眼里没水儿,认了个假货。关键是得罪了真正的队长,人家会认为说书人不把队长放在眼里,没有当回事儿,应管的事儿人家也偏不管,这生意就谈不成了。
我还在犹豫,郭汉就抢先了:“伙计,哪个是队长?介绍一下呗。”
被问者随手一指:“那不是队长!”被指的人立即怼了回去:“你爬那蛋根那歇歇!”立即又指了过去,向着郭汉说,“给你说话的才是队长哩。”
我一看就明白了,不用说,相互指认的两个人,哪一个也不是队长。他们完全是拿说书人开涮,来取笑开心的。果不其然,有个上年纪的好心人看不下去了,指责那两个人:“打啥扎子哩?人家出门人不容易,能成事儿给人家成点事儿,不能成事儿不要(‘不要’促读音:bào)给人家开玩笑。”又转向旁边坐着低头吸烟的中年人,“能说不能,给人家一个囫囵话儿,不要耽误人家的事儿!”
很明显,那个低头吸烟,不说话的人才是真正的队长。“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不失时机地把郭汉领了过去,郭汉掏出“花城”,摸着往队长手里递:“哎哟,队长,俺们有眼不识泰山,失敬了。”队长笑笑,一边推辞着“不吸,不吸”,一边接过续在自己的半截烟上,这才缓缓地说道:“你没看,忙成这,咋说(书)哩?”
还没等我们开口,就有人撺掇:“说书是黑啦说的,也不是白天说的。黑啦还忙球哩忙?跟俺婶子在床上忙咧?”
说话的是一年轻人,肯定是侄儿辈,队长笑骂道:“爬你打那蛋过去!没大没小。我问你哪只耳朵想听说书?把那只耳朵割了。”又转向我们,“他们都想听哩,就先说一段听听吧。”
郭汉说:“中,这不难,拉一张桌子,搬俩凳子,咱就开始。”
大家起哄,荒郊野地的,去哪找桌子、凳子?郭汉说,没桌凳,弦子没法拉,鼓没地方支。有人说:“在外面哩,将就点,来吧,这大石头多光,坐石头上拉不耽误事儿。鼓没地方支,就不要鼓了,狗蛋儿,你坐这石头上,戴着安全帽,叫人家说书的当鼓敲!”又有人笑着接茬儿:“听说过背着鼓寻槌儿,没听说戴着帽寻槌敲哩。”
大家说笑了一回,说书人也只好将就了,坐在石头上拉弦,没地方放鼓,就只打着钢板唱了一段儿书帽。大家拍手起哄:“中,中,中,唱得美!一定得说几场。”
还没等说书人开口,队长就发话:“狗娃儿,你不干活啦,领着说书的回去,晌午就在你家吃饭,黑啦照护着拉桌子,搬板凳,烧开水。支应说书的活儿交给你啦,照样给你记分。”
队长一句话,啥事都下架。按郭汉的说法,这是路上拾的书。意为没有主动联系,顺路拣到的生意。
前面提过,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后,生产队没有了集体经济,涉及花钱的事儿有点作难。说书的虽然钱不多,人少,好支应,被称为“轻骑兵”。但在农村说书还是会给队长找不少麻烦的。先是派饭,常言说,出门人没有带着锅,说书的每到一处,都是管吃、管住。大集体时,那个年代农村吃的欠,队里派给社员家管饭,每人每顿饭,一斤麦子的报酬。一斤麦磨成面管一个人一顿饭绰绰有余,“利润”不小。所以大家争着管饭,队长派饭也好派。连产责任制以后,家家户户粮食打得多了,吃的都不欠啦,没人在乎这一斤麦子的报酬,生的变成熟的,很多人嫌麻烦,轮到派自己家管饭,大多都推三阻四的,比如忙啦,家里没人啦,家里没油盐啦等诸多原因。没人想管饭,队长派饭就作难,派不下去了,就让自己的老婆管,落老婆的一顿埋怨。除了派饭,还得安排说书的住宿,支应说书的桌椅板凳、烟茶等一大堆哆嗦事儿,说罢书临走打发工钱也作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得和会计商量哪处还有余钱,怎样挪用,先打发说书的走……
说实在话,说书的上门确实给队长添了很多麻烦。所以生产队长遭遇说书的事儿,大多都会采用“躲、推、撵”三字方针作对策:先是躲,尽量避开说书的,以免被纠缠得脱不了身;躲不过就推,以各种理由推辞,忙啦,顾不上啦,没有空啦,没有钱啦,等下次啦……;推不掉就撵,好说歹说,说书人还是死缠烂打地不走的话,就只好来硬的,下逐客令, 不走也得走!
说书人吃的就是这门衣饭,要生存,要说书,还非得找队长不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面对生产队长们的“躲、推、撵”三字方针,也总结了一套应对的“四字诀”:问、选、堵、缠。
先说“问”,农村说法也叫“打听”。说书人每到一处,先要打听以下信息:这个村子最近说过书没有。队长一般会以刚说过书为由,措机打发说书的走人。再打听这个村有没有说书的传统,好(爱好)不好听说书。有爱听说书习惯的村,联系成功的几率就很高;如果有史以来,这个村就没有说过书,不用去找,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机会太少,找人家也是白费力。
打听好这个村最近没说过书,又好听说书,两位老师就在村外找个地方等,打发我进村“侦察”队长的有关信息,包括住处、年龄、家庭、喜好(是否好听说书)等。进村问谁,咋问?郭老师也告诉了一些经验。不能问老婆们,上年纪了,嘴絮,哆嗦了半天,也说不出所以然,耽误事儿;不能问年轻小伙,常言说,嘴上没胡,说话转轴,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年轻人爱开玩笑,好毛捣人,说话办事指望不上;大闺女小媳妇不能问,咱出门人得避嫌,人家看你是陌生人,也不会跟你多搭腔,办你丢人;小学生娃们不能问,嘴快,腿快,还没问完,就跑去给队长送信儿,有的队长听到说书人来了会躲避,坏了咱们的大事儿。打听人、问事儿得会问,得讲究策略,旁敲侧击地问,含蓄地问,拐弯抹角地问,有意无意地问……,不能问得太直,不能让对方猜到你的意图,以免泄漏消息,让队长跑掉了,我们找不到。
乖乖,这里边的这些道道儿真能把人绕晕!这哪是在做说书生意,分明是在搞敌特工作,刺探情报哈。
问好这一切,把“情报”搜集得差不多了,开始进入下一步“选”,一是选择最近没有说过书,又好听说书的村子。二是选择有利的时机,午饭前最好,恰好赶在饭点,可以混顿饭吃。队长也是有事人,平时不可能老呆在家中等你去找,但吃饭时候总得回家吃饭吧?瞅准茬口儿,能见到队长的机会就多些。
问好,机会选好,准备就绪,我们一行三人就悄然行动,兵贵神速,直接怼到家门口,把队长“堵”在家里。等到队长发现我们已经晚了,躲也无处躲,藏也无处藏。只好硬着头皮地接待我们。
接下来就是“推”与“缠”的较量。队长推托的理由有多种,每种理由都很充足,有说服力,而说书人死打硬缠的理由并不多,郭汉说得最多的也就是江湖上常说的一句话:“没君子不养艺人。”还有就是“要饭的到你门上也得打发打发吧?”每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心里凉了半截,感到阵阵的寒心和悲哀。唉,原来自己憧憬的说书艺术竟然和讨饭的相提并论!自己下决心要从事的说书行当原来是人们常说的”巧要饭的”。以后十数年的行艺生涯,经历的热嘲冷讽,眉高眼低,也深深印证了跑江湖卖艺,说书行当确实比要饭的强不了多少。
“没君子不养艺人”“要饭的到你门上也得打发打发吧?”这两句话确实能打动不少人,能让大多数队长动容,从而慷慨接纳说书人。大家都想当“君子”,没人想当“小人”。然而也有极个别的队长不吃这一套,任你说破天,口水费干,也不买账,缠也没用。眼看谈不拢,生意难成,临走时郭汉还不忘记说几句难听话:“伙计,你一辈子都不出门啦!要出去非饿死不中!”或者来几句调侃话,讽刺挖苦队长:“伙计,苦去球啦!你这队长是兔子尾巴,发不粗,长(zhang)不长(chang),不带那苔儿!”或者说队长:“说大话,使小钱儿,串亲戚,挎小篮儿,生个娃子一点点儿……”在队长一片尴尬,脸红脖子粗,来不及发作时,昂首挺胸而去。
这就是老师们用实际行动向我传授的“生意经”。出师以后,有的悟其精髓,受用一生,有的因个人性格或时代变迁而弃之不用。轮到自己单独行艺时,生产队几乎不存在了,找队长基本没用啦。行艺环境的变化需要重新探索新一代的,最新版本的“生意经”。此是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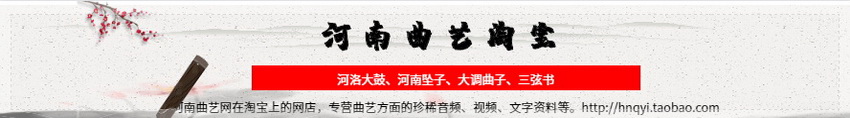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