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坟
吕武成
还没到二月十五,提前几天,居住在新安县的二哥就微信视频过来:“武成,二月十五回去上坟吧?”
我们老家新安县大山以下沿袭河洛风俗,每年的二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为上坟的日子。一直弄不明白一年中为啥要选定在这两个时间点。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也是传统的“鬼节”,传说这一天是地府之王的生日,为了庆贺就会做出大赦,在七月十五当天,地府的大门会敞开,所有的“鬼”都会被释放,可以自由出入凡间,去寻找自己的家人接受祭拜。赶在神鬼们的这个“节假日”上坟烧纸摆贡品,很容易被逝去的亲人认领,所以定在七月十五上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春季为何不赶在国家统一规定的清明节这个公祭日扫墓祭祖,而偏偏要提前到二月十五呢?至今未解。
“往年不都是七月十五回去吗,今年咋搁二月十五啦?”我疑惑。
二哥微信上说了原因:原来七月十五上坟只用坐车到横山村口,坐船回老家很方便。这几年没有渡船了,开车回去得绕新安县到后山转一大圈儿再兜回来。山路崎岖难走,七月天热不说,暴雨多,容易冲毁山路,行车没有把握,安全不能保证。如果山路不通,则只能经路家岭至檀洼山,在对面隔河遥祭。不能亲到父母坟头磕头烧纸,留下遗憾。春天没有暴雨,山路不容易被破坏,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地。所以今年计划将七月十五上坟的日子提前到二月十五。
二哥是我们这一大家的“拿事儿”人,历来说一不二,说是与我商量,不过是走个过场儿,实际上是“软说硬办”。我这个当兄弟的一般很少敢犟嘴、反驳,老老实实地执行“命令”,此次亦然。就回复:“中,你说啥时候都中。”
“那你给小克说说,叫他提前请假。”二哥接着吩咐。
小克是我侄儿,大哥的老三孩子。
移民搬迁后,每年的七月十五,由二哥牵头,我们弟兄三个,结伴回老家看看,一来上坟烧纸,二来给坟头添土。且成了每年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的约定。不管有多忙,抽不开身,都不能成为不回家上坟的理由,有天大的事儿,都先搁下来,放一放,不好意思,也不敢成为推托的借口。约几家乡邻,租几辆面包,带上锨,经横水街买好香箔纸钱,鞭炮祭品,至横山口坐船,经龟山,进平王沟,隔河渡井,风尘仆仆地去看望父母。
原约定弟兄三个回家上坟,一个也不能少。但跑了几年,大哥终被病魔打败,掉了队,舍弃我们,率先过那边陪伴父母去了。大雁三行,少了一只,倍感伤怀,折其手足,何其痛哉!
所幸侄子小克,承先父遗志,步其后尘,代父上坟,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了下来。数年来,每次上坟,侄子总是克服一切困难,该请假的请假,其他事儿该推的推,从没有因迟疑和退却而误事儿。这几年他买了车,上坟方便了不少,不用再花钱租车了,我们也跟着沾了不少光。在这个传统文化,文明礼仪被忽略、遗忘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浮躁、喧嚣和功利而乡情、亲情被冷漠和边缘化的社会,在这个追逐时尚、潮流和前沿化的年轻一代里,侄子小克的行为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一级降(xiàng)一级,二哥吩咐我,我交待小克。小克很是痛快地答应下来,于是,十五那天:“东市买纸钱,西市买炮鞭,旦辞河阳地,驱车回新安。”下了高速,接到二哥,下石寺,越北冶,上刘黄,至驼腰折向东,沿西岭往东北环山而行,过李家沟,翻榆树岭,豁然开朗,故乡的一切尽收眼底,老家在向我们招手了。
|
一眼望见我们老家上坡的土窑洞遗址,六亩地(地名)父母坟墓的位置清晰可辩,直线距离仿佛近在咫尺,但整个平王沟里都是一湾碧波荡漾的湖水,把回家的路隔得十分遥远。须从榆树岭沿山经老王坡、老古嘴、皮老虎嘴、任家岭,才能真正扑进老家母亲的怀抱。而绕这一大圈儿足有三四十里,且是包山的人临时开辟的山路,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且随时都有被大雨冲坏的可能。贸然深入,一旦被困在半路,则进退两难,风险极大。好在选在春季,雨水极少,走这山路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放眼望去,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条蚯蚓似的小道儿,若隐若现地缠绕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着伸向家的方向。依稀看见山岭沟壑间,偶尔有来有往地驶过几辆小车,象屎壳郎般地蠕动。习惯了温孟滩宽畅平坦的柏油路,头一次走这山路,窄得不能再窄,仅能容一辆小车通过,迎面来车,错车都成问题。头一次见这种下山下岭的坡,陡得不能再陡,一旦冲不上去,一旦刹车失灵,后果不堪设想。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家的路,义无反顾。迫切回到老家怀抱的心情,化作力量、胆量和动力。这点危险和困难算啥?挡不住回家的脚步。
小车蜗牛般地,小心翼翼地上山下岭,拐弯抹角儿。开车的专心致志,坐车的提心吊胆。小心之余,还是忍不住看一下窗外风景。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感到那么的亲切、熟悉,充满着情感、回忆和故事。我们指点着,交谈着,感怀着,既兴奋又激动。
初春的二月,春日未暖,花未吐芳,绿色尚在孕育中,到处显得灰冷、萧条、苍凉,朦胧的薄雾飘荡在山间,灰蒙蒙的,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虽不见清明时节的“雨纷纷”,也谈不上路上行人的“欲断魂”,却很能衬托出游子归乡祭祀的心境。偶尔迎面有小车驶来,双方赶忙互相找错车的地方,停下一看,大都是认识的老乡。“借问老乡何处归,回首遥指去上坟。”瞎,杜枚这首诗,叫我篡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算啦,咱不是做诗那块料哈。
|
小车喘着气在山间逶迤,家越来越近,驶到任家岭,下一个小坡儿就是家了。“叔,快看,桃花!”小克惊喜得像发现了新大陆。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对面山上的付家坡满山遍野尽是山桃花,远远望去,似一片粉红色的云,平添了几分祥瑞。按照季节规律,二月杏花开,三月桃花开。二月里桃花芬芳,让人感到奇异和新鲜。
侄媳妇领着两个孙女跳下车来,听说要上坟,高兴得手舞足蹈。看着她们蹦蹦跳跳地窜来窜去,仿佛看到了自己儿时上坟的影子……
故乡上坟习俗已久,记事起,曾跟随父亲和两个哥哥上坟,那时候上的是“老坟”。何谓“老坟”?就是埋的爷爷辈以上几代祖宗的坟,书面语言称“祖坟”,乡下人俗称“老坟”。上老坟的人特别多,叔伯、堂叔伯等没出五服的一大家子聚在一起,把各家各户的祭品统一摆在供桌上,统一烧香表纸箔,坟头上绑白纸,然后长幼有序,从前到后排列,纷纷跪下磕三个响头,接着鸣放鞭炮,就算祭拜完毕。等香头(灰)落了,证明老祖宗已经领了香烟祭品,方可撤供,各自回家。
儿时上坟,懵懵懂懂,不知道啥叫感伤和缅怀。这么多人难得地,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面对着一个个披着荒草的土堆,被大人们强行捺(nàn)着磕头,只觉得好玩。大人们说,只有磕了头,才能抢没有放响的“瞎鞭炮儿”,才有资格分吃上坟后的供食。要知道供食都是平时极难吃到的煎鸡蛋皮、松肉、扁肚和一块块薄闪闪猪肉片子啊,看一眼直让人流口水儿。有些调皮胆大的按捺不住诱惑,想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去偷吃一块儿,立即被喝开:“爬走!爷奶奶还没有吃,哪能轮到你!”
八岁丧父,老坟进(埋)不去人了,于是就有了“新扎莹”。每年上坟,除了上“老坟”外,还多了一个“新坟”,且把父亲的新坟放在了重点。那时还小,仍无法体会丧父之痛,憨憨地扒(盼)着上坟时,图能吃到好东西,唉,少不更事啊。
这都是五十年的陈年旧事了。1999年,千禧年之际,小浪底水库移民搬迁,所有的人和物都搬迁到黄河彼岸的河阳孟州,却把长眠于地下的列祖列宗及生我养我的父母永远地留在了老家,这是很令人伤感和无奈的事儿。新家虽好,故园难舍。故乡山水,魂牵梦绕。留在老家的父母成了无法忘却的牵挂。正因如此,借上坟的日子,每年都要回去转一圈儿,不图别的,就是为了多看一眼家乡的山水,在父母坟前多坐一会儿。
“今年水好大,咱家的坟都淹了啊。”二哥的话把我从回忆中拽回,这才注意到已经来到水边儿,距父母坟墓不远的地方。坟头已经藏在水里,看不见了,山风低鸣,掠过水面,吹皱面前幽幽的一汪湖波,似有无尽哀怨。不知何时飘来一丝愁云,遮挡了本就不是十分亮丽的苍穹,顿感天地苍茫,黯然无光。我们试图披荆斩棘,绕行攀爬,与坟头的位置再接近一些,但被水隔断,徒劳无功。只好原地停下,与父母隔水相望。
|
“哎——”二哥嚎啕大哭起来。按理说,上坟是不能哭的,可二哥每次回去,看到父母坟头时,离老远就涕泪交流,哭得不能自己,让我们同行人跟着泪目。二哥的伤心难过,原因很多:一来想起我们都远走高飞,把父母撇在荒凉之地,好生孤单可怜;二来想起当年弟兄仨同来上坟,如今少了大哥,且自己亦近古稀,上坟的日子屈指可数,岂不感伤?今年又看不到父母的坟头,连近距离陪伴的机会也没有,想到父母泡在水里,不仅二哥,我们所有人都心里酸酸的。
无法接近坟前烧纸祭祀,只好在水边找一平坦的地方,画一大圆圈,开口朝向父母坟头的方向,据说这样才能保护祭品不被外鬼抢去。这一切都是我和侄儿小克在忙活,二哥只是远远地坐着,看着。二哥信教,严守耶酥的规矩,不信神,不上坟,不烧香,不磕头,甚至连祭品也不买。可每次上坟都是二哥在张罗,在督促,临到祭祀的环节,他却袖手旁观。二哥所谓的上坟,任何礼节都没有,只是陪我们回家看看,陪父母坐坐,或是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由于二哥不参与祭祀,坟前上香的事儿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在正中间扒土为炉(香炉),燃香三支,望空绕了三绕,双膝跪下,念念有词:“爹,娘,俺们回来看您们,给您们送吃的,送花的啦!却被水隔着,无法到跟前,你们只好跑步腿啦,没有办法啊。”然后喟然长叹,恭恭敬敬地把香插上。
我不信鬼神,但心中有父母,尤在其时,恍如冥冥之中,人神感应,让人顿生敬畏;我不轻易下跪,但跪天跪地跪父母,天经地义,心悦诚服,让人不得不屈膝。这一跪,跪出了心酸愧疚;这一跪,跪出了五味杂陈。二哥用哭来表达对逝者的追思和伤感,而我内向,一切尽在不言中,包含在磕下的重重的三个响头里。
上坟的祭品和纸钱也在与时俱进。早年的上坟,祭品是很有讲究,精心准备的,蒸供品专用的花馍称为“供香”,做供品专用的菜称为“摆菜”或“摆碗儿”。摆碗儿用的都是平时难以吃到的高档菜,如松肉、扁肚、鸡蛋、猪肉等,但不能用粉条儿,据说上坟摆粉条儿,后辈孩子鼻涕多……现在时代发展了,人也懒了,很少有人摆菜,图省事儿大多买些点心水果之类的充当供品。专供鬼花的钱原来是金箔银箔的,现在也变成和人民币相仿的纸币了。
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人死如灯灭,带的供品再丰盛,烧的纸钱再多,逝者在哪里?能看得见,吃得到,花得着吗?恐怕连气儿也闻不到,连面儿也见不着!是啊,祭品,只是活着人的一片心意和念想;上坟,也不过是一种纪念活动;坟头压纸可以证明有人上过坟,这个坟有子孙后代……仅此而已。
侄子摆上各式各样的点心、水果,点烧纸钱,庄重地跪下磕头。又一阵风旋来,把燃烧的纸灰催起了老高,在空中飞舞。烧香人说过:焚烧纸钱的灰烬如果飘不起来,说明亲人没有领到银钱和衣服;飘得越高,越远,停留的时间越长,表示祭祀的礼品逝者高高兴兴地收到了。想到此处,心中掠过一丝欣慰,静静地看着袅袅升起的香烟,伴着东风飘向父母坟墓的方向。
大哥活着的时候,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辞,却懂得很多。他说,香通三界,烟透九霄。阴阳相隔不能见,千呼万唤难听见。我们用文字,用语言,只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寄托,都不可能送达对方。唯一能在阴阳之间传递信息,沟通交流的工具只有香烟。据说,焚香便是向逝者发起的邀请和召唤,香烟飘起,无论亲人的鬼魂在天涯海角,都能收到信息,闻香而至,接受亲人的祭拜。
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只能依靠香烟与父母对话,以达到心有灵犀的默契。河洛习俗,无论上坟祭祀,还是十月一烧寒衣,都要烧香。先烧上香,才能摆祭品,烧纸钱等。祭祀罢,必须要等香灰落了,才算逝者认领已毕,方可撤供。香灰落了,我们静坐在原地,仍不愿离开,一年只能回来一次,想多陪父母一会儿。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不结束的陪伴。依依不舍,终有一别。当收拾东西,一步一回首,距父母渐行渐远之时,心中默念,自言自语:“爹,娘,安息吧!明年再回来看您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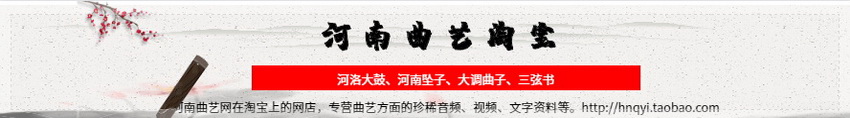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