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六
尽管郭汉老师在大山以下混得比较熟,人缘好,人脉广,且在联系说书生意广面有一套儿本事,深谐“生意之道”,“生意经”运用自如。但在一个地方演唱三天以上,所谓“坐住窝儿”的生意很少,大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时还“放空炮”,跑一天没揽住“活儿”。书没有多说,腿没少跑,地方没少转。先是从寺村桥经石寺,奔曹村,直达城崖地,至渑池边界折回,绕山碧、田岭、北岭,复回石寺川。恰巧转了一个大圈儿又回到原地。老师埋怨,都怪刚出门头一天我让他们坐到碾盘上了,才有这“转圈儿生意”。下一步往哪走?郭汉脚一 跺:“球,先到俺老丈人家歇歇再说!”
郭汉老师的岳父家是古寺下古灯村的。那时还没结婚,未过门的女婿路途奔波,一路风尘,灰头土脸地前去投亲。大 家失魂落魄的狼狈样儿,我都感觉不好意思,有点难为情,到亲戚门上恐遭人白眼,被人低看。人家郭汉老师才不理会这个,大咧咧地说:“球!老丈人家咋着?照去不误!”
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仍得到了热情款待。只是妻嫂子看着郭汉长扎扎,乱糟糟的罗圈胡子,笑着说:“汉儿,看你这鳖样儿吧。赶紧滚去古灯铝矿去洗洗澡,给你那毛儿褪褪!”在老家把猪杀死后,烧一锅滚水烫烫,把毛去掉,叫“褪毛”,比作人身上,是一句骂人的话。郭汉笑着还口:“不褪,长到我脸上啦,又没长你脸上,胡子再长也扎不住你。”
说笑归说笑,郭汉还是和我们一道去洗澡。古灯铝矿是国营矿,规模很大。头一次来到此地,感觉好象一个“小洛阳”一般,高楼林立,几条街道甚是热闹、红火,各种商店,各种服务设施应有尽有。澡堂很大,很豪华的样子。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洗去连日来的灰尘和疲惫,顿感神清气爽。洗罢澡,路过饭店,门口支着卤猪锅,卤着猪肉和各种杂碎,香喷喷地诱人。郭汉眼不好使,鼻子特灵,闻到卤肉味了,走不动了:“进去吃卤肉!”王老师不太乐意:“没有挣着钱儿,吃啥哩吃?”郭汉说:“球,没钱也得吃,我掏钱!只当昨天那一卦白算啦。”又说起常挂在嘴边儿的那句话,“逮个鳖,吃半月,逮个鳖儿籽儿,吃不大一会儿。昨天算卦的钱,今天吃卤肉!”说着推着我的肩膀进了饭店。
掌柜的迎上来,问吃啥哩。郭汉放着那么多猪肉不吃,偏要点很贵的猪蹄儿。啃猪蹄儿也有窍门,得会啃。看出来郭汉吃猪蹄并不擅长,弄得手上、脸上、胡子上都是猪油,肉沫儿,吃相很难看。还没啃几口,一失手掉地上了,恰巧桌子下卧着一条狗。这只狗一看高兴了,咦,这个人不错,发善心了,扔给我一个猪蹄吃,二话不说,叼起就跑。郭汉看不见,还说:“武成,快给我拾起来。”我说:“不用拾了,叫狗噙跑啦。”郭汉一顿足:“他打那蛋,我算是给狗买了个猪蹄儿!”王老师笑得吃到嘴里的肉喷了出来,我捂着嘴偷笑得肚子疼,又不敢大声笑,怕郭老师训我。
在下古灯做短暂的停留,休整,准备折向南,朝庙头、铁门一带挺进。我们大山下人把五头、正村一带称为“东坡顶上”,新安县庙头、铁门在新安县西,称为“西坡顶上”。从古灯沿畛河川走到尽头,开始上一架大坡,坡长足有二三十里,上去坡放眼望去,远远地就看见了庙头村。我们从清早起身,到庙头时已经临近傍晚,走了十来个小时。有的问,那个时候不通“票车”(公共汽车)吗?通啊,七几年通车的县城与北大山以下的交通主线“新狂公路”(新安至狂口),就是经过庙头和石寺,最多两个小时就能遇见一辆“票车”,但我们不坐。王老师说,出门做生意,禁忌坐车。原因有二:车是跑的,寓意“生意会放跑”;生意是在路上慢慢遇的,不是坐车跑出来的,车上跑不出来生意。我嘴里不说,心里嘀咕,说啥忌讳这,禁忌那的,不过是心疼那两块钱车票罢啦。
这一天运气不错,没有白跑,天黑时,我们在过庙头不远的省庄扎住了书场。二位老师一番推辞以后,我垫场,郭汉领大书(说大部头),开正本儿,王老师拉弦侍候。
王老师和郭汉老师厮跟得少,两个人的大书套不到一块儿,不能轮换着同说一部大书。王老师擅说《彩楼记》和《刘镛下南京》,是拾王何清的书。怎么拾的?是王何清把书弄丢了,俺老师拾住啦?哈哈,不是那个意思。这是河洛大鼓行内约定俗成的说法,没有正式学过,跟他人一遍一遍地听,听得多了,逐渐学会的书,称之为“拾书”。这两部书郭汉老师不会。郭汉老师擅说《金钱记》和《大宋剑侠三宝图》,是跟他老师王管子学的。两个人会的书不同,说书风格也不太相同。王老师说书比较严谨,没有彻底学会,完全掌握,达不到一定熟练程度的书,决不会往外“卖”,擅说“死口儿书”,唱腔、调门儿、书词都是固定的,即死腔、死调、死词儿,一般不会轻易更改。郭汉则善说“活口儿书”,唱腔、调门儿、书词唱一回一个样,回回不一样,即活腔、活调儿、活词儿。用俺老师的话说,郭汉是“憨胆大”,有的书听别人介绍一点故事情节,似懂非懂的,就敢往外卖。知道一点儿“大荒样儿”,照住那一角子就敢着(zhào)。王老师嫌郭老师说书不讲究,太粗,“胡球弄”。郭老师则嫌王老师死搬硬套,不灵活,“日死逼手儿”。王老师开的大书不想让郭汉接茬儿,害怕把书说跑了,说差周了,自己不好接,收不住缰。郭老师开的大书王老师不想接,不想象郭汉一样的胡来。这种情形下,俩人只好一人开大书,一人专门伴奏了。
一般情况下,王老师开大书的多,比郭老师的书更容易获得听众的认可。但这一次来了个大逆袭,郭汉唱的《大宋剑侠三宝图》“叫好儿”了,相反,王老师的书却没有“打响”。说书这一行和其它行当不一样。其它行业技术高的,本事大的,干点巧活,轻活,指指点点的,不用出力,还能拿高工资;没有技术,没啥本领的,只有干重活、脏活、累活,待遇还低。说书的却不然,你艺术高,说得好,观众就不放过你,一个劲地让你说,活该出大力,流大汗,不累趴下不能算;你艺不惊人,观众不买账,就是想说,观众也不让你张嘴,想出力也没地方出,老牤牛掉井里,有气力也使唤不上,反倒可以图个清闲。
省庄这五天书,可把郭汉老师累得够呛。第三天头上啜子已经哑了,王老师心疼他,加上自己坐“冷板凳”也很不好意思,想替他抵挡一把。刚往书桌后一站,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有听众开腔啦:“你歇歇,还叫那个低个儿的罗圈胡说吧。”一句话,不软不硬地把王老师给“轰”了下来,弄了个“老长脸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过后王老师自我解嘲地笑着说:“郭汉成‘香丁丁’,我成‘臭百毛’啦。”
观众不买王老师的“账”,他倒也落个清闲自在,少操了不少心,趁这个机会,领着我去离省庄不远,有二三里地的下羊义拜访了他的算卦老师张得星。
王老师的算命批八字之术是跟铁门下羊义的张得星学的。张德星不仅通晓阴阳,精通四柱八字,而且说书功夫也频有造诣。后来才知道,张得星是宜阳盐镇的洛阳琴艺人书田林子的得意弟子,起初也是洛阳琴书出身,五几年洛阳琴书没落,河洛大鼓兴起,就见风使舵,改唱河洛大鼓,频具影响力,与新安县第三代著名艺人王震松各成一派,平分秋色。
我们见到张得星那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失目人行动不便,加上年纪大了,早已不再出门行艺。一个人抱着一根长棍,孤零零地坐在大门以里的门洞里,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时间,家人端过一碗饭塞给他之外,再没有过多的话语。邻居们偶尔到他家串门儿,或打门口经过,视而无睹,彼此并不打招呼。他看不到别人,别人似乎也没发现他,把他当成了空气。
张得星大师坐在门洞里面一动也没动地接待了我们,没有惊喜,也没有伤感,平静如水。虽然是俺老师的算卦老师,但这次他们几乎没有探讨批八字方面的内容,谈得最多的却是说书。王老师把我介绍给他,说是新收的徒弟。他点点头,算是作了回答。我对这位看似清瘦,却透着不凡气质的老者很感兴趣,极力央求老者唱一段听听,学习学习。再三的请求下,才找出来已经生锈的钢板,递到张老手上。张老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在王老师的弦子声中,缓缓开唱。他唱的是一段劝世文:
太阳星好比一张耧,转通世界把地搜(原字是‘cou’音,这个字写不出来,只好用‘搜’代替)。北斗星帮耧指方向,东西风好象曳楼的牛。一天一趟来往转,月光摇耧定稀稠。世上人好比楼中籽,摇来摇去土里头。六十岁以前人吃土,六十岁以后入土口。人吃黄土常欢乐,土吃人肉一旦休。光阴没有回头路,长江不见水倒流。观众们爱听老实话,争名夺利莫强求。得到欢乐且欢乐,该吃酒肉就吃酒。生产季节勤劳动,休息时间要享受。积于金银装满库,到头来两拳落空手,盖起了高楼并大厦,临死时落副木壳娄。哎,仔细想,看破红尘淡如水,人活世间有几秋!
张老唱这段时,可能联想到自己年轻时风光,晚景凄凉的处境吧,借以抒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伤感情怀。整段唱腔沙哑中透着苍凉,伤感与哀怨交织。当唱到“唉,仔细想,看破尘世淡如水”时,用的是“大叹腔”唱法,唱腔不断下行,声音更加低沉、厚重,让听者心头上象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顿生窒息之感。唱段已终,意犹未尽,让人沉浸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可能这就是我很少听过,老师给我介绍过的河洛大鼓“老调儿”。也许张得星是直接从洛阳琴书改行河洛大鼓的,唱腔中或多或少地残留有洛阳琴书的影子。总之让我眼界大开,领略到和老师他们那种“新调儿”迴然不同的韵味。很多送腔、拐弯的地方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最后的一句叹腔“看破尘世淡如水”,运腔、行腔都非常地巧妙。可惜那时没有录音条件,不能有效地留存。在以后的学艺生涯中,这句叹腔我反复尝试着学唱,学来学去,终究也没有那个味儿,时至今日,我只记得那种唱法很美,但已经无法复制了。
有的说,你记性不赖呀,人家唱一遍儿,你就把词记得这样清楚?咦,看我多大本事哩,向来是忘性超过记性。是我当时听这一段词好,立即拿出纸笔,人家说一句,我记一句抄下来背会的。不但抄会了这一段儿,还抄了一段比较长的劝家书段《揪老虎》。大致内容是:黄河北孟县城有弟兄两个,娶了两个媳妇,生了两个孩子。本来和睦之家,因小弟俩争夺一个玩具皮老虎,把老虎头揪掉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先是俩小孩儿打架,引起妯娌两个生气,进而弟兄两个大打出手,最后闹到分家,为了半亩地之争,打官司打了三年,家业贴个净光。最后告诫世人,如果听了媳妇的话,弟兄们搁合不长久。这段劝家书很有教育意义,我也很喜欢唱,观众们也很喜欢听。
此次访师之行,虽然短暂,有些唱腔技巧连皮毛也没学到,小有遗憾,但得此两段书,几乎受益一生,也算是收获满满吧。以致许多年后,每当唱起这两段书的时候,便想起了那个独坐门洞里,佝偻、消瘦、孤独的身影。
省庄说书之后,重启奔波劳累之旅。六月末旬,正值中伏,酷热难当。伏里天的热是湿热,闷热,感觉压抑,透不过来气的热。行走在路上,当老师们不住地擦着汗,商量着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我打起了“退堂鼓”:“水热天气,人太受罪。叫我说不胜先回家歇歇吧,等凉快了再出来吧。”话一出口,立即遭到劈头盖脸地一顿训斥:“天凉快?天凉快秋就熟了,出来不成啦!才出门儿几天,可想回家哩!就这点出息,咋能学成说书?你当出门是好吃的白糖果子?出门人就是受罪的,不受苦中苦,难熬人上人!想学说书,就得学会吃苦,不想学的话,哪凉快往哪里去!”
这一顿骂,呛得我哑口无言,再不敢多说一句话,领着他俩继续赶路。这一天,跑了几个村,到处碰壁,到处吃“闭门羹”。天黑了,在庙头西北记不得叫什么名字的村子找到队长,好话说八千,唾沫星费半碗。怎奈队长滴水不进,任你说破天,只有两个字,不中!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郭汉说:“就是说不成书,天黑了,俺们哪也去不成了,总得找个地方住下吧?”队长仍然摇头:“没地方住!”王老师说:“想想办法吧,队长,出门人难。随便找个地方将就一下吧,好店只一宿。”队长被缠得没了脾气,只好拉过一张苇席,两条被单儿,领我们到不远处的一孔草窑,指着里面盛放着的半窑麦秸:“今夜就在这里将就一下吧。”
这是我说书以来,也是以后十数年里遭遇最差、最糟糕的一次待遇——住草窑!记得老母亲曾多次说过,出门人能遇到草窑就是“神仙窝儿”,最暖和,冷天时候不受罪。我不以为然,草窑是盛草的,哪是住人的。想不到今天实实在在地轮到我头上了,第一次体验到“神仙窝儿”的滋味。“神仙窝儿”是指冬天而言,夏天呢?简直是“魔窖”!
草窑里面黑漆漆的,没有灯,也不敢点灯。老师他们都是吸烟人,随身带有打火机,也不敢使用,怕“引火烧身”。郭汉烟瘾大,急着吸烟咋办?很简单两个字:憋住!我嘟囔着:“没有灯,啥也看不见,席都没法铺。”王老师说:“过一边去,看俺们咋铺哩。”
唉,我一个明眼人,没有光线,反倒成了“瞎子”。对两个失目人来说,已经摸习惯了,有灯没灯一个样,灯对他们来说,纯属多余。你看他俩一个比一个能,熟练地摸索着把麦秸摊平,把苇席放正,把被单伸展,干净麻利。我象个木桩似的在一边儿站着,什么也做不了。说来好笑,本来我是侍候他俩的,现在倒好,角色倒置,该轮到他俩为我服务了。
忙碌过后,大家摸黑趟了下来。谁都没有睡着,谁也不想说话,白天的奔波,屡次的受挫,让人没有心绪多说一句话。晚饭没吃成,窝囊气倒装满一肚子,把饥饿挤一边去了。草窑里不通风,身底下的麦秸让人热得烦躁。蚊子非常热情好客,贴在耳边唱歌,绕来绕去地亲热,瞅空儿冷不丁还要“吻”上一口,死打烂缠,驱之不散。身子底下说不清是虱子,还是虼蚤,对侵犯它们的“领土”表示强烈的愤慨和抗议,时不时地瞅准机会进行“反击”,咬一下换个地方,找都不好找。
躺在席上,翻来履去地睡不着,脑子也翻江倒海般地想了很多。唉,只道说书的人前仰脸高看,人后高接远送,想不到今日也能遭这种罪!热得难受,汗水顺脊梁沟往下流,浸湿了身下的席子,就想起了家里的土窑洞,才是真正的“神仙洞”啊,冬暖夏凉!三伏天,不管再热,回到家往床上一躺,暑意顿消,不用吊扇,不用空调,那叫一个凉快,一个舒适惬意。晚上没吃饭,说不饥,那是气话。饥肠碌碌,便想起了母亲做的面叶儿稀饭,喝两碗不饥不喝;想起了老娘擀的红薯面条儿,凉水一冰,泼点“蒜水儿”,“吐噜、吐噜”来两碗,那叫个得劲儿!好想回家,好想睡家里的破土窑,好想娘亲,好想娘的红薯面条!好后悔,后悔不该学这破说书的,娘常说出门人难,想不到出门人会这样难!好恨,恨老师不近人情,想回家都不批准,还乱训人!越想越鳖屈,越想越心灰意冷。管他哩,不让回家我偏要回!趁他们好象睡着的机会,先偷跑回去再说,至于他们咋办,也顾不少恁多了。相到这里,就悄悄地摸出草窑,走上大路,朝家的方向飞奔。
半夜里,外面的酷热已经散去,凉爽了不少,回家的路,轻松自在。跑路特别有精神,特别快,似乎插上了翅膀,不多一会儿就飞到了庙上山顶,下坡感觉象驾云一样,轻飘飘的。快下去坡时一看,傻眼啦!面前的畛河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汪洋一片,水茫茫地不见边际。不由得心生疑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要建小浪底水库,我们的家会淹没。咋说建就建呢,家咋说淹就淹呢?忽然想起,哎呀,我的家在哪,我的娘呢,我的亲人呢?刹那间,着急要回的“家”变得非常渺茫,遥不可及,不由一阵扎心般地难受。正茫然无助,忽见洪水正急剧上涨,脚下的路正不断地被吞噬!来不及多想,忙抽身往上跑。水上涨的速度比跑路还快,不由得又急又怕,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冥冥中,隐约有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想喊,喊不出声。阵阵恶臭迎面扑来,令人作呕,肚子们的酸水不住地往下涌,“哇”地哕了出来……
“武成,你这是咋啦?”迷糊中,感受到了哕出来的秽物难闻的气味,感觉到王老师正在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焦急地问。这才醒转,闹半天是南柯一梦。郭汉老师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象火炭一样,惊得跳了起来:“哎呀,烧成这,咋办哩?”
王老师也是急得团团转:“哎呀,这三更半夜哩,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去寻大夫,到哪去拾药?”
知道他们的难处,明眼人尚且作难,何况眼睛又都看不见,行动不便,上哪里找人看病?看他们着急的样子,心中一热,颇感不忍,就安慰他们:“不要紧,刚才哕出来,心里好受多啦,没多大事儿。放心睡吧,明天再说。”
他们叹口气,也只能这样了。接下来我昏昏沉沉沉,似睡非睡的,嘴里不住地说胡话,说的啥自己也不知道。只感觉一会儿回到家,看到母亲的笑容了;一会儿又感觉娘在前面不慌不忙地走,我在后面一溜小跑地撵,却总也撵不上。急切地想喊娘等等我,嘴里边却发不出声音,急得手足乱颤。醒转过来,又胡思乱想一番。如果在家,有个头疼脑热的,母亲昼夜守候,做一碗擀得薄闪闪,切得细溜溜,煮得软和和的酸汤面,加上辣椒油儿,亲手端到床前,递到手里,亲眼看着喝下,说发发汗就好了。如今他乡异土,举目无亲,病困草窑,由谁来疼?想到此,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想哭又不敢哭出声,怕惊动老师们担心,笑我没出息。
第二天早上,感觉好了不少。老师又摸了摸我的额头,仍有些发烫,便不再坚持“不能回家”的决定了。当机立断,把我送回家中。也不再心疼那两块钱车费了,直接坐上车,“哧”地一下,可到仓头啦。恁快?你没听说飞机快,大炮快,都赶不上俺说书的嘴快?十万八千里,嘴角冒股风就到了,何况只有几十里路?
下了车,趟过畛河,觉得浑身轻松,心情舒畅了不少。老师又摸了摸我的额头,凉凉的,一点也不热了,问我:“还烧不烧?”我回答:“早好了,不烧啦。”老师笑着数落:“你这娃子,这病是想回家想的,还是想回家装出来的?给俺们吓得可不轻。”
我也笑了,装也罢,不装也可,反正是到家啦。
二十多天没回家,感觉好像过了两年多,穷家难舍,一切都感到亲切,到处都是熟悉的味道。母亲看到我们,没有说话,泪先落了下来,擦着眼泪说:“你们可回来啦!昨晚我做了个梦可不好,担心你们在外面有事儿,想不到今早上可回来啦。”
王老师笑着说:“本来俺们不打算回来的,你家(方言促读音‘niá’)武成非要回来,不让他回来,就有病,把俺们吓死啦。担不了这个担儿,就送回来了。”
母亲笑得泪又流了出来:“娃们儿长恁大没出过门儿,时间长不回家,我也应急啊。回来好,回来好!”
我在一边默默地想,儿想娘,娘盼儿,心有灵犀一点通。昨晚做梦想娘,娘同一时刻也做梦想儿,这是一种母子亲情之间不约而同的信息感应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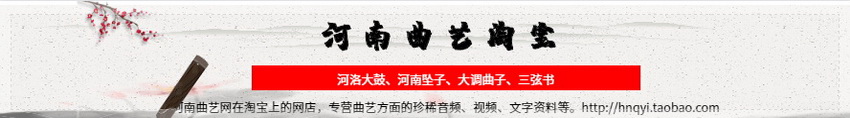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