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十几年了,从未回去过。父亲回去过一次,看照片,那道山沟已成了水库,所有的一切只余苍茫的水面和几座露出水面的山头。
多年前,当我还是个村野孩童的时候,故乡寺上村坐落在两座并行的山之间,山间一道小溪蜿蜒而过。
山不甚高,大自然既没赐它怡人的景色,也没给他鬼斧神工的造化,水却极好,打山下淌过,四季不断。一旁的山腹中还流出一股清泉,夏日炎炎,附在岩石边上直接啜饮,清冽甘美,暑气尽消,造福了无数远行的路人和一整个村子。那时很重要的一项家务,便是用桶挑水回家。满满两桶水压得母亲肩上的扁担颤颤巍巍,迈着细碎的步子前行,溅出的水滴在地下留着一道细细的水印。
桑葚
山上有一些果树,桑葚成熟的季节,和几个哥哥一起上山,一个人爬上树摘,其他人在下面一边捡一边往嘴里塞,吃得嘴成了黑紫色,指着对方的嘴笑。依稀记得还有几颗柿树,柿子熟透的时候,摘起来一定要格外小心,一不小心掉在地上便暴殄天物了。成熟的柿子似乎马上要流出来,要开一个小口,汁液滑过舌尖,流过喉咙,粘滞住味蕾,总舍不得立刻吃完。
大学时,斑驳的机电馆门前,路旁有几颗桑树,成熟的时节,落下的桑葚被行人踩过,在地上留下点点黑斑,我路过很多次,也终是没捡起过一颗。
槐花
每当山上槐花盛开,满树缀满稠密的花瓣,洁白中透着淡淡的鹅黄,拿了长长的钩子从树上折下几枝,小心避开枝上的尖刺,用手轻轻一捋便有了一捧花瓣,直接塞进嘴里,香甜可口。剩余的花瓣和着面放在锅里蒸出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99年移民搬迁,来到了孟州的黄河滩区安下新家之后,村子后面有一大片人工林,几乎满满全是槐树。春日槐花绽放,高中每周末骑车从学校回家时经过树林边上,就会看到有养蜂人在一堆蜂箱前忙活,大群的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只是再没吃过槐花。
花生
那真的是个零食匮乏的年代,七毛钱一袋的方便面都觉得很奢侈。幸运的是,地里却可以长出怎么吃都吃不完的零食。
知了的叫声听起来总是不可思议地绵长,仿佛要贯穿了整个夏季,花生椭圆的叶片在无风的夏日纹丝不动,路过地头的母亲随手拔起一棵看看长势,然后甩甩上面的泥土,摘下花生随手递给一旁的我。这时节的花生还带着泥土的气息,剥开外壳,透着水分的果实带着一丝甜味,嚼起来满口生津。
花生成熟以后从地里刨出,摊成一片,晒到搅动的时候有哗啦啦的清脆声音便收起来,随时剥开都是一样的香甜。有时则架上一口铁锅,放进一些沙子,再把花生倒进去不断翻炒。出锅的花生剥开后,轻轻搓掉一层皮,原本洁白的果仁带着淡淡的焦黄色,带着焦味的香气早抢在味蕾之前袭来。
红薯
直到现在,当我在街上看到卖烤红薯的小摊,还是有种特殊的感觉。小时候家里蒸馒头,差不多锅里一半都是红薯,煮汤时也会放上一些红薯。
故乡的山上有一部分是贫瘠的沙土地,红薯却格外高产,收获的季节,抱着一块特别大的给父母看。有时晚上烙饼,母亲在鏊子周围放上一圈红薯切成的薄片,来回翻动几次后,香甜的气息便四散开来,烤到微焦,轻轻掰开,被禁锢久了的甜香便随着丝丝白汽爆裂开来。有一部分收获的红薯会就地制成薄片,铺满漫山遍野晾晒,待红薯片干脆之后磨碎放在几口大缸里沉淀数天,最后制成的红薯淀粉则是另一种美妙的食材了,制成面条是黑色,入口爽滑甘甜,也可以拌上萝卜丝蒸熟,然后炒来吃,至今仍是逢年过节家中饭桌必备的一道菜。
现在想来,这不挑土地的食粮却给当时的生活带来许多甘甜。
手擀面
作为一个河南人,对面条有着很深的感情,母亲擀出的面条宽窄粗细都恰到好处,离家久了,最想吃的是一碗手擀面。
现在的我也会在晚上饿的时候下楼买几包零食消灭掉,偶尔呼朋唤友找家饭馆大快朵颐,喝得微醺迎风笑谈。可是偶尔想起那些只有来自田野的零食的日子,才感觉远去许久了。
好几次在市里想找家面馆尝尝看有没有家乡的味道,最后却还是在肯德基对付一顿了事离家许久了,有时走得远了,忽然就忘了来时的路。
一路走来二十余年,大学在沈阳,工作在长春,两地都距离家乡一千多公里,每年春节踏上归家的旅途时,总有一丝兴奋和忐忑。不管是距离还是时间,当它要夺走你的回忆的时候,我们的抵抗都显得那么无力。多年前的村野孩童在山间溪边留下多少足迹,而今只剩模糊的记忆碎片可供捡拾。
从前,小溪很浅,时光很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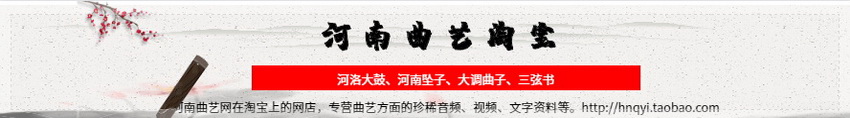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