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台湾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杨秀芳女士在台大校史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河洛话 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
杨秀芳女士是台湾知名学者,在学界享有一定声誉。
单单一个“成”字,在河洛话中就有xing(行)、xia(霞)、qia(恰)、jia(家)四个读音。而一字两音、一字三音,在河洛话中大量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杨秀芳女士认为:一字多读的语言现象,是由历史上多次北方居民南迁带来的多层次语言累积而成,反映了河洛话形成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话至少可以分秦汉、南北朝、唐宋三个层次。而河洛话中,一字两读、三读乃至多读正好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面,就像考古学上不同朝代的土层一样。一字多读,可说是多层次古汉语的古音遗存。
以“石”字为例,河洛话中,说“石头”时,石念作“jiu(九)”,是秦汉时期古音的反映;说“石榴”时,“石”念作“xia(霞)”,是南北朝古音的反映;说读书音时,“石”念作“xie(写)”,是唐宋时期古音的反映。
杨秀芳说,河洛话,堪称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研究河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河洛话和中原古汉语有密切的语言联系。
河洛话不分轻、重唇音和“端系”、“知系”
中原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古汉语入声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已经消失,而河洛话入声仍然存在,四声各分阴阳,成为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俗称八音。其中阳上和阳去恰好在声调上是同一个调值,合并成“阳去”,所以实际上有七种音调。
台湾“河洛郎”把“芳”念作“滂”,“飞”念作“杯”,“蜂”念作“滂”,“河洛郎”一般发不出“f”这个齿唇擦音,轻唇音读如重唇音;“河洛郎”说话时,常把“猪”念作“滴”,在语言学中,是“端系”和“知系”不分。
这是为什么呢?杨秀芳女士认为,河洛话之所以轻、重唇音不分,“端系”和“知系”不分,就是因为河洛话反映了唐代以前的中原古汉语的特点。
在唐代,古汉语的重唇音分裂产生了轻唇音,而“端系”、“知系”也发生分化,所以现在的洛阳孩子可以很容易地发“f”、“zh”这两个音;因为福建偏居 东南一隅,相对闭塞,河洛话(闽南语)仍然保持唐代之前古汉语的发音特点,没有跟上唐代这一大的语音变化,所以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方言系统。
河洛话和洛阳方言是“亲戚”却分属不同方言系统
很多洛阳人会感到奇怪:既然洛阳人和“河洛郎”是“亲戚”,那为啥台湾人说的河洛话咱们洛阳人一句也听不懂?
杨秀芳女士说,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曾经详细区分“中国十大方言”,分别是官话、晋、吴、徽、湘、赣、客、粤、平话、闽。洛阳地处中原,和北方各 地联系紧密、互动密切,所以从方言学上说,洛阳方言和北京方言一样,属于官话系统;河洛话则属于相对封闭的闽方言系统。两种方言虽然是“亲戚”,却属于 “远亲”,不属于同一个方言系统。
河洛话和洛阳方言仍有部分字词发音相似
既然河洛话和洛阳方言不属于同一方言系统,但“河洛郎”和洛阳人是“亲戚”,是亲戚,就会有相通的血脉。
杨秀芳女士肯定地说:河洛话和洛阳方言仍有部分字词发音相似。
杨秀芳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洛阳方言辞典》,笑着说:河洛话说“日头”,而洛阳方言也说“日头”; 河洛话有“雨蒙蒙”的说法,洛阳人也说“蒙蒙雨”;在描述下雨、下雪时,河洛话和洛阳方言都会说成“落雨”、“落雪”;天气晴朗,洛阳人和“河洛郎”都会 用“好天”来形容;形容用手或瓢洒水的动作,洛阳人和“河洛郎”都说“戽” ,念作“huo(或)水”……
“河洛郎”长期生活在台湾,虽然受台湾原住民影响,有一小部分词汇来自原住民语言,又因日本殖民统治五十年而使用一些日语借词,但从整体来说,河洛话来源于中原古汉语,和洛阳方言是“亲戚”这一说法不容置疑。
“洛阳的朋友不妨到台湾走一走、看一看,好好和‘河洛郎’聊聊,您一定会发现,洛阳方言和河洛话存在很多相似点。”采访结束时,杨秀芳笑着向洛阳人发出邀请。(程奇)(原标题:河洛话: 洛阳方言的“亲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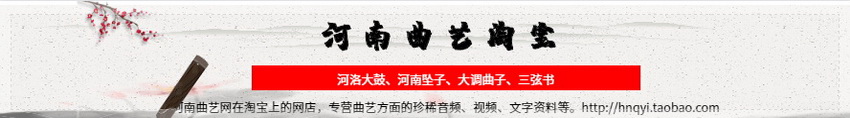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