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打了三二百斤
小说
吕武成
蜿蜒于温孟滩的移民大道,一字长蛇阵摊满了黄澄澄、金灿灿的玉米。远远望去,宛若游龙,黑黢黢的柏油马路,摇身一变,成了一条泛着金光的黄龙,煞是壮观。东去西行的汽车只能小心翼翼地蜗行在被挤占剩下的三分之一路面上。遇上迎面来车,双方须相互谦让,提前在两家玉米交界的空隙处错车。司机不但要避免碾压粮食,更要躲过隔三差五竖在粮食边沿上的啤酒瓶。

尽管“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的规定已经喊了多年,但乡官村吏们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了。因为基层的官儿大都是从土地里走出来的,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咋走,即使没种过地也知道种地人的不易。你不让农民在路上晒粮食,让他到哪晒去?总不能摊到自己家的锅台上吧。
在这一片连一片,持续数里的玉米长龙里,中间最长、最黄、最饱满的那一段儿便是秋生家的玉米了。
秋生用“搅麦耙儿”挨个儿把玉米搅了一遍。那“沙沙沙”翻搅粮食的声音似一曲美妙的音乐,让人听得悦耳、陶醉。然后站在路边,摸出口袋里的半盒“十渠”,抖出一根叼在嘴里,用打火机慢吞吞地点上,潇洒地把火苗甩灭,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儿。反复地打量着自家那金黄的玉米,像欣赏自己的一副得意佳作,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自豪,一双略显浑黄的眼球似乎放着希望的光。
六零后的秋生对秋有着不解之缘,六十年前的那个秋季他降生了,秋生的名字由此而起。吃着秋长大的秋生,又种着秋变老,一辈子对秋情有独钟,尤其喜欢侍弄玉米。
秋生今年种了十亩玉米。相比动则数十亩甚至数百亩的“包地大户”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比起一家一户来说,十亩玉米已经相当不少了。秋生不但种自己家的一亩多责任田,还承包了在城买房没人耕种的其他两户土地,也算是小“种地户”啦。
种地不仅靠勤劳,还得凭运气。今夏老天爷照顾得不错,风调雨顺、无灾无害、无旱无涝。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按庄稼人的说法,就是“秋成啦”。较往年的收成,一亩地要多打个三二百斤,十亩地下来,就是三两千斤哪。秋生想想都兴奋,略显佝偻的腰杆儿往上挺了挺,有些笔直起来。
“收玉米的咋还不来?”望着已经晒干的玉米,秋生喃喃自语。搁往年这时候,收粮食的大机动三轮这个不走那个来,“收玉米”“收茭茭”的声音此起彼伏。今年呢,连收玉米的影儿也不见。“收玉米的都他妈的死哪去啦。”秋生心里忿忿地骂。
说曹操,曹操到。正念叨着,就听见秋风里隐隐约约传来“收玉米,收玉米”的吆叫声,且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顺着声音望去,见一辆大机动三轮正沿着公路朝这边驶来。“收玉米”的声音就是从车头小喇叭里传出来的。秋生就像听见了天籁之音:收秋季节,哪会没有收玉米的?这不是来了嘛。
多年卖粮食,秋生已经积累下经验,摸着些门道儿:做生意你寻着他和他找到你不一样。常言说,买急遇不着卖急,卖急遇不着买急。慌啥?沉住气不少打粮食,呵呵,不对,应该是沉住气不少卖钱。秋生拿定主意:收粮食的如果不停下车来问自己,他绝对不会上前拦车求卖;只有人家停车找上门来,才能讨价还价。于是,迎面驶过来的收粮食车,秋生视而不见,故意背过身子,做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出乎意料的是,收粮食的车一边喊着“收玉米”,一边紧贴着玉米长龙擦身而过,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经过秋生身边时,并没有发生预见的,像往常一样司机从司机笼里伸出头来,大声地问:“喂,玉米卖不卖?”这个熊司机,好像脑子进水,眼神不好使,把一路上这么多的玉米当成了空气,把竖在路边的秋生当成了一截木头似的,硬是“两眼不望窗外事,一心只握方向盘”,瞎。
“傻逼一个!”望着擦肩而过的收粮食车,秋生忿忿地骂着,却顿感失落。收玉米的见玉米不闻不问,不应该呀。唉,早知道就不该拿架子,拦住车问一句儿价格又能小到哪去?秋生寄希望与其他同伴儿,那么多家呢,总有人出头吧?
果不其然,车没走多远,便被人拦了下来。司机跳下车,扒拉了几下玉米,又拾起两颗丢嘴里咬了咬,几个人围着好像在说价钱。没多大功夫,司机摇了摇头,摆了摆手,坐上车一溜烟地走了。
“啥价?”秋生赶了过去,见车已走远,就问几个乡亲。
“他妈的,根本说不成事儿,你都想不着他会给啥价,八毛!”乡亲有点气急败坏。
“啥,八毛?”秋生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也太离谱了吧!这两三年玉米价格一直萎靡不振,去年一斤一块已经极不划算了,今年不奢望涨到哪去,但也不能落成这样啊。每年新玉米大量下地,造成一时过剩,收购商趁机压低价格也很正常,但总不能砍价砍到骨头缝里还再加一刀,这不是要人的命吗?
“咱农民种点地,十八根肋子乱动弹,一点血一滴汗的,想拾便宜,没门儿!”大伙儿的态度很强硬。
“都嫑急。”面对乡亲们的满腹牢骚,秋生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大秋刚下来,这不才开始收嘛。咱们都稳住,价格不到位,谁也别出手。他们收不来玉米,自然会涨价的。”
“秋生说得是。你种了恁多玉米还不急哩,俺们慌个啥?再等等吧。”
这一等,两三天过去了。每天都上映着同样的镜头:不断来收玉米的,不断地拦截,不断地磨嘴皮子搞价钱,又一个个不断地放跑。收玉米的先后来了不下二十家,公路上摊的玉米却丝纹不动,一点也不见少。大伙儿拉弓放箭,软磨硬泡,软硬兼施,嘴皮磨破,口水费干,招数使尽,价格仍在原地踏步。所有收玉米的好像事先串通好似的,八毛的价格牢不可破,想涨一分都不可能,而且临走还撂下话来,再等等价格还会落。
晒干的玉米老摊在公路上卖不出去不是个事啊。不仅大伙都沉不住气,秋生也坐不住了。金灿灿珍珠似的玉米,却成了烫手的山芋,拿也不是,扔也不是。
秋生种了一二十年的玉米,经历了潮起潮落。曾几何时,玉米的身价一路飙升,从六毛多噌噌地往上飞,一跃竟然超过小麦的价格涨到一块二三,最高峰时竟能卖到一块四五。随后便“小偷下四川,一年不如一年”,一路下跌,直至去年降到了一块。粮食价格上扬,地本儿、化肥、农药、机械、人工跟着水涨船高。粮食价格回落,已经浮上去的所有成本却居高不下,不降反升。这几年早已入不敷出,粮贱伤农,想种地的人已经不多了。尤其是玉米跌到一块后,更没人想种,面积已经大幅度减少,但秋生和为数不多的十几户仍在顽强地坚持。
秋生他们之所以在玉米行情长期低迷时仍不放手,自有其中的道理。一来是人称的“种地迷”,种了一辈子的玉米,已经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不种就感觉少点啥。二来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根据经验和市场规律,种地和做生意一样:有一涨,必有一跌;有一跌,必有一涨。涨时跟风,跌时吃亏;跌时入手,涨时渔利。秋生他们就是认准了玉米已经跌入低谷,山穷水尽之际,正是峰回路转之时。说不定来年严冬已过,定然回春。因此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狠狠地赌上一把。谁料玉米价格一落再落,这一赌输得更苦、更惨。
一想到辛辛苦苦种的十亩玉米刨去成本费用,不说自己搭进去的功夫,劳不尽的心血,恐怕连投进去的资金也捞不回来。秋生的心在往下沉,脸色像灰破鞋甩的一样灰溜溜难看,眼神顿时黯然无光,本已驼背的腰弯得更很,像虾米一样直不起来了。
“娘的,八毛钱一斤!倒沟里让水冲走,扔地里沤粪也不卖!”有人撂下狠话。
“倒沟里,扔地里?烧棉袄气虱哩?血本无归,没人心疼你,还会让人看笑话。这不是一句气话嘛。”有人接茬儿。
“不卖啦!有货不算贫客。装到袋子拉回家囤起来,等行情好了再出手。我都不信,咱拿着猪头寻不下庙门啦。”有人赌气。
立即遭到反驳:“装装拉拉来回折腾,费的不是你气力?这时候卖不出去,等行情好至少也得过去年。玉米越放越轻,即便能涨个一二分,却又丢了多少舍头儿?能划算吗?”
“就是。东西窝到手里,变不成钱,花啥?赊的化肥农药钱咋打发?新农合、养老保险拿啥缴?总不能屁股撅起来叫人家踢吧?”有人附和。
大伙儿默然。在过去的说法是,农民只要有地种,就有饭吃,就饿不死。现在不同了,有地种,有饭吃,没钱花还真活不下去。要是踢个响屁股能抵合作医疗的话,情愿叫人家踢,不行啊。唉,庄稼人土里刨食容易,土里刨钱,难哪。
“哎,干吗姜太公钓鱼,守着鱼钩死等?咱不如自己把玉米送到收粮食点儿,也省去一道贩子的盘剥,说不定还能多得二分哩。”又有人出了个招儿。
“这倒是个好主意。”有几个人响应,“谁有收粮食点儿的联系方式,问一下,合适了咱就直接送去。”
“我有。竹园的裴保国这些年一直做粮食生意,前年投资五十多万盖了一个收购存贮点儿,规模超大,方圆数十里的粮贩儿收的粮食都卖到他那去啦。要不咱打电话探探虚实?”有人提供信息。
“不用问。”立即有人否定,“竹园的保国我还不清楚?去年一块钱一斤,囤了七八百吨,结果今年麦前八毛五一斤出手,赔进去二三十万。都吃亏姓‘裴’,这一下‘赔’得翻不过来身了。别说‘保国’啦,连自己的老本儿都保不住。你听说他今年收过粮食?早不干啦。”
“那……,竹园不中,咱不会再问问别处的粮食点儿,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可拉倒吧,天下老鸹一般黑,上门生意难做。你送去试试?别说人家推三阻四,就是收你的,湿啦、瘪啦、水分大啦、杂质多啦,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压你磅,扣你秤,宰你没商量。货到地头儿死,费力气拉去了,总不能再拉回吧,只有挨坑的份儿。”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议论来议论去的,也没想出来个好主意。最后统一意见:拉弓不能拉断,扳价钱不能扳脱。该出手时就出手,识时务者为俊杰。再来收粮食的车,说啥也得卖,不能再等了。
来啦!“收茭茭,收茭茭——”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孟州当地人。移民村沿袭新安老家的叫法,把玉米称“玉蜀黍”,孟州话却唤“茭茭”。
还没轮到秋生开口,早就有人将车拦下,问:“啥价?”
“好的八毛。”司机一边回答,一边停住下车。
“太便宜啦,前一个月还八毛五哩,咋又落了五分?”
收玉米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当地人,做起生意来,相比新安县过来的移民要和气、精明得多。有人搞价钱,不急、不燥、不恼,耐心地笑着解释:“老怀(孟州话,老伙计),一个月以前的是春玉米,量小价钱大,现在秋玉米大量下地,价格就回落了。管你打听管你问,到哪里都是这个价。市场行情,谁也没办法。”
“谁信?粮站也是八毛?”
“粮站八毛二还要除杂质扣秤。俺们收粮食的投着本金,吃苦受累担风险,见一斤也就摸个一二分的。说句良心话,我也是种地的,知道种地不容易,可做生意更难。这年月,钱难挣,屎难吃。”
这个收玉米的会说话,会来事儿。虽说买卖心不合,但“种地不容易”这句话在收粮食和卖粮食之间却瞬间拉近距离,唤起共鸣,引发了共同话题。
“唉,今年的玉米价格为啥低成这?”有人困惑。
收玉米的很健谈,把生意放在一边儿,却和大伙儿一块扯起闲话,拉起了家常:“老怀,你知道玉米价格低的原因吗?你没看手机上的新闻头条?咱国家从美国进口了很多很多的玉米,你知道多钱一斤不?除去运费、关税等一切费用,才合五毛多,便宜得很。你想,收咱老百姓的玉米给八毛多,国家是不是还照顾着咱农民哩?”
“呵呵,俺们也听说有这事儿。真弄不明白,咱农民自己种的粮食生产过剩,卖不出去,为啥还要去进口老美的粮食呢?”有人不解。
收玉米人说:“老怀,国与国之间的事儿,咱们小老百姓谁能说得清楚?网上有人议论,说国家正在下一盘大棋,咋个走法,咱普通人哪能知道?反正就是大量的进口玉米充斥市场,把咱农民自产的玉米逼到了死角,变得一文不值。咱有啥办法?”
“唉,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把土地流产啦。”有人开始吃后悔药。
“呵呵,没文化真可怕。是‘流转’,可不是‘流产’。国家这样做,就是让农民种地不挣钱,然后自己把土地流转出去……”
“哎,哎,打住,打住。”收玉米人急忙制止,“咱农民只管种地,莫谈国事。田间地头说话,哪说哪了,嫑往外说啊。”
大伙儿都在高谈阔论,秋生在一旁蹲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无意插话,心里却想了很多。
前几年土地流转,村里挨家挨户征取村民意见。大多数人都签了字,立了合同。唯有秋生和其他的一二十户顽固不化,死活不同意。无奈之下,村里只好划出一片土地给他们重新调整分配。现在落得如此光景,秋生有点悔不当初了。不是后悔自己不会种地,打不出来粮食,而是后悔种出来的粮食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作为农民,他永远弄不明白:为什么这几年粮食连年丰收,却连年落不住钱;为什么春耕夏耘,辛勤劳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越过越穷。为什么,为什么!?
他还弄不明白:化肥农药的价钱,生产厂家、经销商说了算;新农合、养老保险交多少,政府说了算;房子卖多高,医院花多少,开发商、医院说了算。可咱农民自己种出来的粮食,价高价低,为什么不能自己说了算?他更弄不明白:新农合一路飞涨,从十块狂飙到四百,想过农民的感受没有?农资涨、物价涨、农民的粮食为啥不涨反降?高昂的房价不能降,泡沫不能刺破,害怕经济崩溃,唯有农民粮食的价格可以随意打压、下调,农民的血汗可以任意压榨、索取,农民的尊严、价值可以肆意踩在脚下蹂躏、践踏。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
一连几个“为什么”让秋生气往上涌,呼吸急促。恍惚中,救世主出现,伸出无比巨大的手,隐隐地说:“来,我扶你一把。”却反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透不过气来。头顶上的天,刹那间变成了一张无边无际的网,黑暗暗、阴沉沉地落下,把他罩在里面,挣脱不得。进而,仿佛那张网又化作重重的三座大山,压得他本已佝偻的腰更弯,弯成了半圆……
“嗨,卖不卖?”的声音把秋生从幻觉中唤醒,见大伙儿包括收玉米的都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他,在征询他的意见。他的玉米最多,大伙儿得靠他拿主意。
“不能再添点儿?”秋生做最后的争取。
“真是添不了啦,老怀。”收玉米人一脸无奈。
“卖!”秋生跺了一下脚,把手上的烟头儿狠狠地扔出老远。
很快,玉米相继装上了车,相继过了电子磅,相继出现滴滴滴的扫码声,看不见、摸不着,或多或少的一串数字相继从收玉米人的手机里飘出,钻进卖粮人的微信哩。而这串数字只是在微信零钱里做短暂的逗留,便开始分流于农资店、医保卡、社保卡以及各个二维码。数字不断变小,直至归零。
数字归零,一年的辛苦归零。然后再从零做起,赊化肥,赊种子,赊农药,赊耕种款,来年卖粮食的这个时候,再用微信扫码归还。
农民复农民,种地复种地,年年复年年,归零复归零……
作者简介:
吕武成,韩愈故里孟州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孟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编撰、整理出版《河洛大鼓》《河洛大鼓志》及《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之一至五等十余部个人专著。创作的曲艺作品《鼠药计》《贬潮州》及《即将凋谢的艺苑之秀-河洛大鼓》获省级奖项,并在《河南曲艺》《洛阳月谈》等刊物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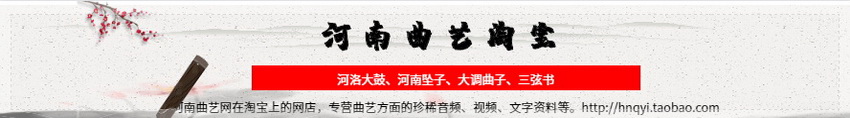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